

吴晓波:靠什么拯救我们的商业人生。
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应邀到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他住在荣巷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钱穆问当时的中国首富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
接着,荣德生突然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他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
前些年写《跌荡一百年》,造访至无锡,当地人带我遍走荣家遗迹,花枝烂漫的梅园,已成废址的工厂,繁华转眼成空,依然屹立的是石桥。荣德生果然说对了。当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消费和享受之后,它的拥有者将如何处之,这是一个比创造这些财富更为艰难的命题。
二
从来没有人因为富甲一时而长久地被人们纪念,相反,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及相关的细节。乔治·盖洛普博士说:“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如何、战功多大、拥有多少财富,而只因为他们的有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
我曾经编著过一本《首富》,写的是全球当今三十个国家的首富。我得出这些结论:这些被人们仰望着的三十个首富,在性格上确乎非常像一枚硬币:低调、坚硬、圆润,貌似不近人情。他们中间,只有一位有过三次婚姻经验,五位有两次,其余均为一次。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看来始终是财富得以循序累进的前提。
三十个首富中,没有科学家、没有作家、艺术家,甚至没有出名的艺术鉴赏家。一定要为这些富豪寻找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的话,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财富与慈善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做给世人看的。一半以上的首富是他们国家中最大的慈善捐赠人。
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此,任何个人也不例外。
三
这十多年来,读得次数最多的书之一,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原因两个,一是薄,二是没懂通。
韦伯第一次揭示了“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渊源关系,他论证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毕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但他们对这笔财富的消费却不感兴趣。韦伯认为,那种源于达尔文宿命学说的生命观念,使得那些人勤俭、自律、诚信、清洁、对单纯娱乐非常厌恶,对劳动的热爱对应成为“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称之为“新教精神”,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成功的精神起源。
事实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丰富和不可思议,而人类在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则面临越来越急迫和严厉的拷问。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财富拥有者都被迫直面这样的困扰。在这本小册子里,韦伯反复言及的,大概只有两个词:贪婪与控制。
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于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对财富的贪欲确实是从商者的最大敌人,如何克服,他的药方是新教伦理。读到这里,就一直读不下去了,因为,中国人从来是入世的。
四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拯救才刚刚开始。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抽象的形而上的信仰。与西方的商业伦理精神相比,中国式的自我拯救似乎更加的具象。千年以来,我们从来只相信现世,即便是匍匐在香火缭绕的庙堂,我们还是在乞求佛祖让我们今世身体健康、财源广进,而来世能够投胎进富贵人家。我们从来没有原罪感,没有生而为赎罪的道德前提,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卢梭看来,这是公民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起点。
那么靠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商业人生?
我们现在有的是:制度的约束,这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多商业行为是完全边缘化的,甚至是界于合法与不合理之间;我曾请教很多人。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告诉我,答案是新儒家伦理,在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他顺手写下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张载的立心、立命及开太平,跟平头百姓有什么关系?我在无数个乡村和读本中行走。黄河青山,中国人千百年来信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足以流传和让他们为之牺牲的?
我期望得到的答案,好像仍然在大雾弥漫之中。

去哪儿今日正式纽交所上市最大融资额1 47亿美元。...

重庆银行H股上市终亮相助力小微企业融资突围。三家...

乳粉行业重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业界仍有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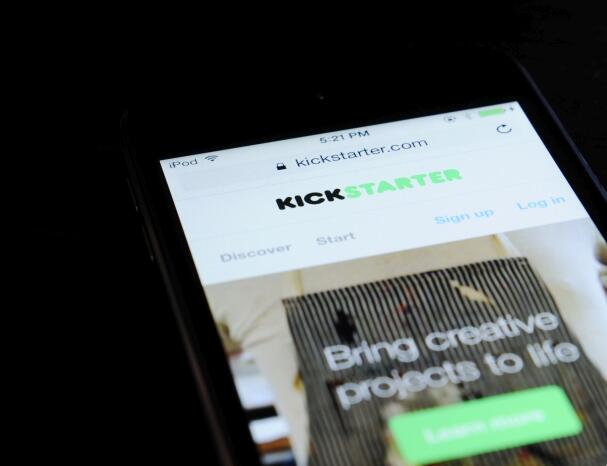
众筹平台Kickstarter迎来里程碑发展成功融资项目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