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晓波:中国经济改革能否跳出“周期律”。
统一,经济治理的核心思想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历朝历代在经济治理方面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吴晓波:维持中央集权制的经济路线,其根源是中国人惧怕分裂。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大规模的人口消灭和城市毁灭,在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痕。还有地理原因。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有大量的平原地区,另一方面建筑又是以土木为主,城市很容易被毁灭,一把火就烧光了,造成的破坏极大,所以确实不适合分裂。
因此,统一就成了中华民族天然的、最强大的终极性文化。要保持国家的稳定,各个地方必须听从一个大脑的指挥,经济权力的集中就成为了一个必然性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从来没有另外一种制度能够维持统一。
环球人物杂志:中央集权对中国经济正面、积极的影响在哪些方面?
吴晓波:很多人将中央集权与独裁专制画等号,却很少看到它在历史上对中国文明和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农耕文明时期,中央集权能保持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工商业的兴盛是跟人口的增长有很大关系的。西汉时,中国人口已过5000万,到了北宋人口过亿,乾隆时超过3.5亿。正是因为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才形成了内需的繁荣,保持长期的稳定局面。在手工业时期,中国的工商文明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雕刻业、制造业、灌溉技术,等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长期稳定和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使中国古代的文明和经济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这些都是中央集权所极力维持的大一统局面带来的,所以古人才有“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看法。
到今天,仍然是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中国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时间最长的可持续增长。除了中国,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30年。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似乎更强调这种模式的负面影响,其弊端是什么?
吴晓波:民族的进取心会大幅度降低,特别是明朝以后,我们为了维持统一付出了拒绝发展的代价。朱元璋北面修长城,断绝了我们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之后南面又禁海运,变成闭关锁国的状态。还有我们对宗教文明的拒绝,将其看成异端邪说,因为儒家文明太发达了。而科举制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精英分子开始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也使得思想的竞争和冲突变得非常弱小,中国人的创造力被禁锢住了。
环球人物杂志:中央集权带来的问题今天能否解决?
吴晓波:这是个胎里结。从汉到清,中国一直没有办法破解。民国初期的十几年里,曾经有过一个联省自治的时期,各省发展各省的经济,但那场实验也是不成功的,在南京政府的统一后画上了句号。陈炯明、张学良、阎锡山……这些人后来在历史书中被称为地方军阀,我们仍然没有从经济治理的角度认真吸取当年联省自治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就看我们这代或下代有没有能力解决了。首先,今天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有很多进步,法律也开始制约政府的权力;第二,古代的统一涉及人口争夺、耕地争夺、水源争夺,而现在处于信息化革命的时期,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的出现,让我们对人口、土地、资源的理解都跟古人有很大的区别。未来的中国人可能会对国家的概念、国家存在的理由、国家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等问题有更新的理解。当这个问题被化解掉后,可能历史上的很多执念就会放下来。
国有资本集团自古就有
环球人物杂志: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有哪些方面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
吴晓波: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国治理模式。今天我们在经济上仍然讲全国一盘棋,中央集权、宏观调控。二是在产业经济层面,始终存在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国有资本集团。
环球人物杂志:能具体讲讲为什么国有资本始终存在吗?
吴晓波:中国是重商主义的国家,从管仲变法到汉武帝变法,确立了一个治理原则,就是国家要控制重要的能源性、资源性产业,从中获利。古代的财政部门有三个司,其中一个是盐铁司,类似于现在的发改委、国资委。所以说,国家从商业中获得利润的思想古已有之。国外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有底层、没有顶层,因为统治者很重视工商业资本的利益获得,所以顶层的能源、资源领域从古至今都被国家控制着。
然而中国又是一个轻商人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的治理原则导致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产业经济领域中的博弈,国有资本会有意识地压制民营资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商人地位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经济领域,儒家一直奉行农耕文明的逻辑:轻徭薄赋、仁义治国、以农为本。隋唐以后,知识分子被科举考试控制住了,但四书五经里并没有一本经济学著作。因此,中国在治理思想上基本杜绝了经济学思考。在民众的普遍意识中,商人是属于末流的。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商人的地位也是偏低的。
环球人物杂志:国有资本集团的历史存在,未来是要打破还是延续?
吴晓波:这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合理性。中国有很多自由派经济学家提出,国有经济没有存在的必要,国资委应该解散,把国有资产按一人一股的方式分给大家。第二,如果国有经济必须存在,那么其存在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存在于哪些领域,跟民营资本是什么关系,形成的国有资产该怎么处置,怎么全民化,国有企业该怎么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我认为第二个问题将是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之一。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有合理性吗?
吴晓波:中外历史都证明,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国有资本很难跟民营资本进行长期竞争。因为民营资本有先天的产权清晰的优势,而且民营资本家是拿性命去竞争的,而国有资本是经理人制度。经理人和创业家之间,长期看确实很难竞争,所以只能通过政策方式形成壁垒,保护国有经济的某些权益。这到底有没有正当性,在经济学界还是一个重大的争议。西方经济学是全然反对的,但在中国,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中国历史上看,保有一定的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该怎么竞争,国有企业该怎么治理,国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有资本的积累该怎么进行重新分配,都是可以讨论的。未来几年,在可操作层面的国有经济改革会被推进。
稳定70年必获大繁荣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有什么规律?
吴晓波: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给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的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10年可恢复,30年可振兴,50年到70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但是,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环球人物杂志:历史上很多次经济变革似乎都导致了经济萎缩或崩溃?
吴晓波:可以这么说。比如汉武帝的变法,到后期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国强民弱,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商品经济趋于衰竭。王莽变法是一次理想主义的实验,包括货币改革、土地国有化改革、对产业经济的国家垄断等,胡适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但由于其理想色彩过重,太激进,很快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和帝国的灭亡。王安石的变法更全面,是帝制时代最后一次整体配套改革,但也过于激进,导致国民经济的萎缩,更严重的后果是打击了民族自信。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之后则变得谨小慎微,更倾向于闭关锁国。可以说,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就是稳定。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改革,你如何评价?
吴晓波:1978年之后的改革我觉得历史还是会给予很高评价的。这30多年来,我们在思想解放、经济模式的创新方面,比古人和我们周边国家快很多。但也要看到,目前的很多难题都是历史性的。而且,这30多年来改革的成功,本质上是一次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一次务实主义的改革。在早期是没有顶层设计的,允许民间和地方政府发挥改革主动性,即使到了1993年搞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以后,很多政策也是随着全球化和国内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这个周期很长,现在还在调整中。
分权和均富的两种类型
环球人物杂志: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的周期律能被打破吗?
吴晓波:我不知道。我写的书其实是在描述这些场景,从中看到一些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可能性,但也没有能力提出一个终极性的解决方案。中国历史很难被预言,即使发生一个变化,也比我们想象的漫长很多,国民和观察者都要有足够的耐心。
但是,我认为人的进步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前提和最核心因素,随着“80后”“90后”的成长,他们的很多思想不再被权威主义或专制思想所束缚。今天的我们很难预测20年后的人们会对国家做出哪些改善或积极选择,我相信一定会有,只是现在不知道会出现在哪个时间点,以什么样的方式,由哪个阶层发动,但我还是坚决地相信人是一定在进步的。
环球人物杂志:针对眼前的经济问题,目前能看到的解决策略是什么?
吴晓波: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治理的主题只有两个:一是分权,二是均富。分权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以及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中央财政及一百多家中央企业的获利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是将大幅增加。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比如通过税制改革,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来继续做大“蛋糕”。
均富也分为两类:政府与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环球人物杂志:从历史上看,中国似乎无法复制任何国家的模式和道路。
吴晓波:我同意,中国一定会走一条自己的道路。现在我们已经走在跟西方不太一样的道路上了,治理结构、经济模式、财富创造的领域和方式,跟西方都不一样。这无所谓好与坏,在意识传统如此不同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跟西方完全一样。很多矛盾会被发展所掩盖,但很多问题也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驱动改革的整个方向还是看得到的。

去哪儿今日正式纽交所上市最大融资额1 47亿美元。...

重庆银行H股上市终亮相助力小微企业融资突围。三家...

乳粉行业重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业界仍有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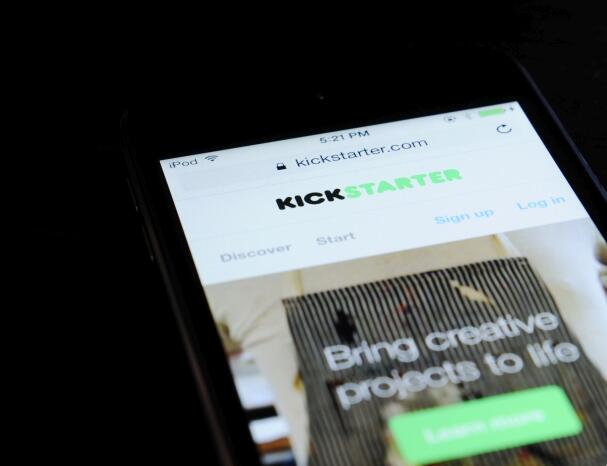
众筹平台Kickstarter迎来里程碑发展成功融资项目超...